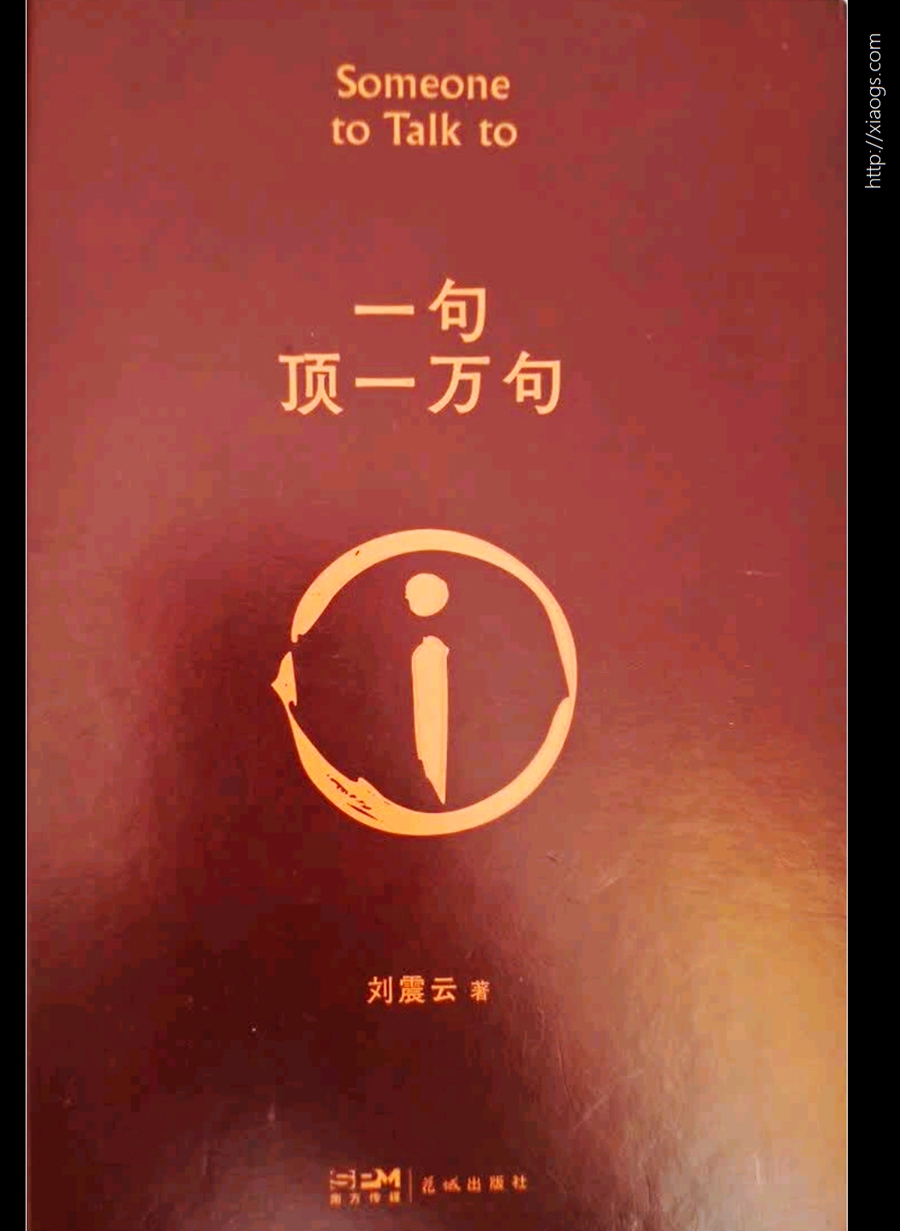
刘震云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冯小刚有关,在这些年又是越捧越高,被改成的电影包括《一地鸡毛》、《一九四二》、《手机》、《我不是潘金莲》等等,而小说中地位最高的便是这本《一句顶一万句》。不过也改编成了电影,只是导演不是冯小刚,而是他自己的女儿,所以拍的不好,知名度不高,评价也比较低。
以前读过的书,基本都是纸质书,偶尔读完电子书,也会买本纸质书。不是怕电子书伤眼,也不是非要弄本纸质书摆书架上,而是觉得日子富裕了些,多少想给作者点支持。这本书读完,发觉电子书的读感要好于纸质书,不是说它带着方便,而是上面很多网友的分享和感悟比自己读起来要有价值得多。
它确实有点像《百年孤独》,只是少了些奇幻怪异,也没有通过人名去把那种宿命轮回的事情挑明,但多多少少也在影射一代代人之间的宿命轴痕。读完这本书再回想《百年孤独》,感受也颇深了些。但它们核心是不同的,刘震云讲的是世上的事绕来绕去,归根到底也就是个说得着和说不着,无非是看你码得清还是码不清。
分享几个感受吧:
一是最回味的一句话,便是最后一句:
牛爱国:不,得找。
找谁?大家心知肚明,毕竟日子是过以后而不是过从前。
二是最赚人眼泪的,无疑是被人贩子拐走的巧玲的一生:
我知道俺奶为啥敲床了。她说过,她小时怕黑,肯定想带一把手电。
巧玲怕黑,而曹青娥不怕黑,所以到死时,曹青娥终于变回了巧玲。当初和吴摩西在一起的时候,吴摩西和吴香香吵架后睡在外卖的柴火堆,巧玲一个人在晚上找到了吴摩西。吴摩西问她为什么不怕黑,巧玲说带了手电。其实是那个时候,巧玲找爹的心战胜了怕黑的心。如今她又要独自一人上路了,周遭已没有了可说话的人,又要怕黑了。
读书时,一直希望曹青娥,也就是之前的曹改心,也就是出延津之前的吴巧玲,能够和她爸,不是他的养爸温家庄的老曹,也不是他亲爸姜记弹花铺的姜虎,而是她的继爸,也就是那个最后改名成罗长礼的吴摩西,也就是杨摩西,也就是杨家庄卖豆腐家的杨百顺重新见面,可惜最后没有。
三是最让人深思的,是我们日常打交道最多的“给”和“要”的关系:
“看啥?他不打包,说明他老实;他一打包,证明我没看错,这孩子有心眼,我不敢要”。待走到船边,杨百顺已将货扛完。半截棉袄都被汗打湿了。老顾三人上船,如果这时杨百顺跟老顾搭讪,杨百顺的大包就白扛了;但杨百顺见到老顾之后,并无表功的意思,看老顾没收留他的意思,也没说啥,本来可以跟他们同乘一条船,到黄河对面,现在也不乘了,跳下船,向小宋招手。他这一跳船,一招手,老顾心动了,觉得他是个憨厚孩子,便向他招手:“小子,上来吧,去染坊让俺家掌柜看一看。他收你,是你的福气;不收你,你也埋怨不着我”。
中国人的“给”和“要”,是个很高深的学问,要学一辈子,不学又不行。很多时候,我可以给,但你不能要,你伸手要了,我就一下子不想给了。一是我不喜欢被人伸手要,打心里就看不上伸手要的人。你诚意表达了即可,再多做就是讨好,一讨好就让人看轻了你。二是我主动给说明我自己明事理,被你一要后,反而显得我不懂事了,还需要你提醒。那便不给了,不但不给,还得说本就不该给,免得让人觉得我不明事理。
四是我们骨子里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也不必隐晦:
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处,也就作罢。
我们很多人,其实一辈子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要比别人幸福。自己过得不好,能忍,可一旦别人过得比我好,往往就心生了嫉妒,也就忍下去了。而这,往往是很多不开心、不幸福的根结。如何能平常心,是个本事。
五是小说里的日子:
父母、兄弟姐妹、夫妻、朋友,离不开又相互折磨。不是在享受日子、过日子,而是在熬日子,熬到彼此没有了脾气,日子就真的成了日子。所以让人记住一句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
“再说点别的”。“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其实,若是说得着,一句也就顶了一万句。
no comment untill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