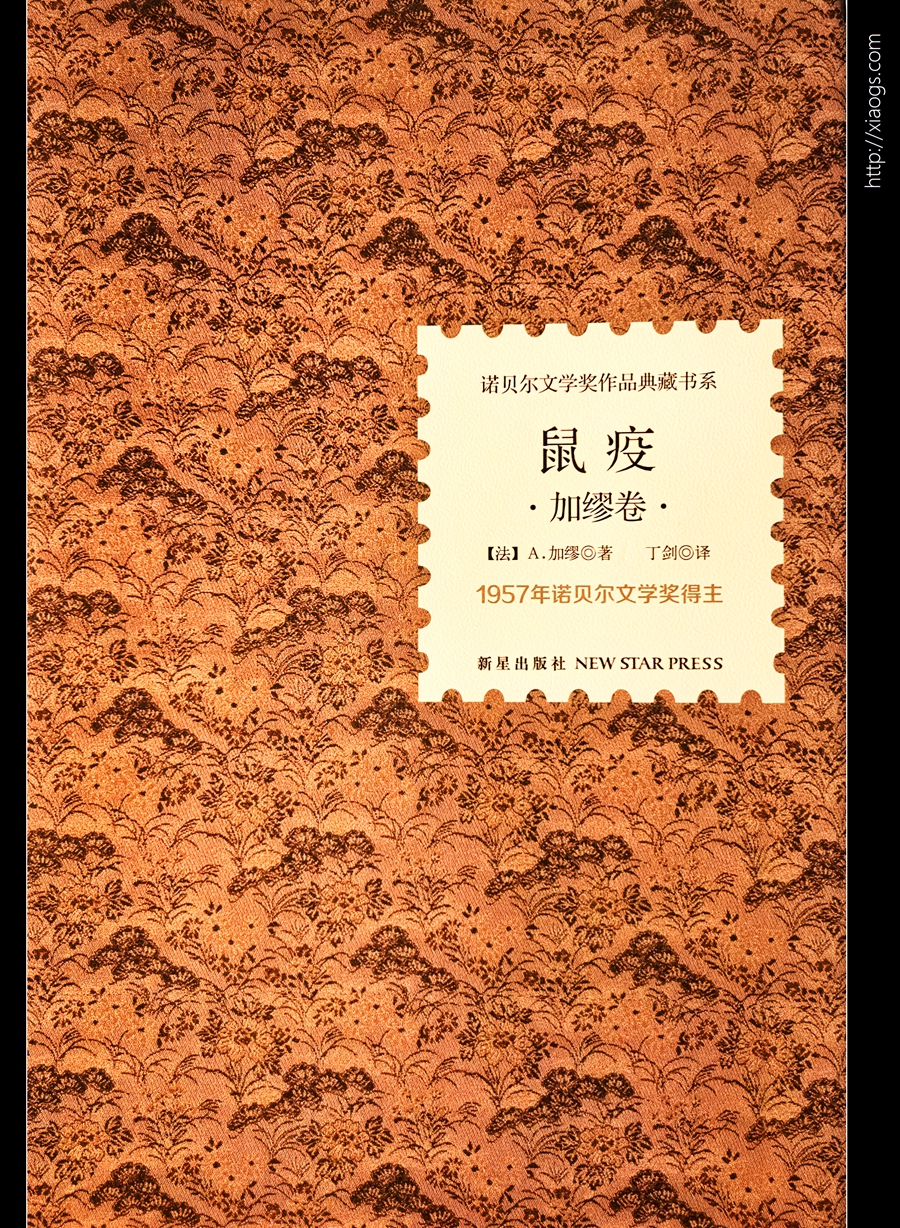
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结束后的今天,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感受颇深。我想,若是没有过切身经历,对于很多事情是难以产生共鸣的。经历过疫情的扫码、检测、隔离、封城之后,才明了真实、事实、现实。
第一个感受,作者描绘的100年前的社会和当今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若是把时间尺度继续放大,会发现即使数百年、上千年以来,人类社会里进步的只是科学和技术,而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社会治理上的事,并无多大变化,人心和人性,更没有什么改变。摘录几个方面:
“起初,还准许打长途电话,结果电话亭给挤爆了,而且长时间占线,一连几天就完全中断电话通信。继而严格限制,只有在所谓的紧急情况下,即有人死亡、出生和结婚时才能通长话。因此,我们就剩下电报这个唯一通信手段了。由智慧、感情和肉体紧密相连的一些人,现在无可奈何,只能从由十个词组成的电文的大写字母中,寻觅昔日情投意合的迹象。电文中实际的可用语式很快就搜罗净尽,因而长期的共同生活,或者痛苦的恋情,很快都高度概括,定期以”我好。想你。爱你”等现成用语交流”。
“纸张供应日渐趋紧,有些期刊不得不削减篇幅,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家新报,《鼠疫信使报》创刊了,其宗旨就是’以十分严格的客观态度,向我们的同胞报道鼠疫的进展或消退的情况,提供有关鼠疫前景的最具权威的判断;设立多种栏目,以支持所有准备同这场灾难做斗争的知名或不知名人士,振作民众的士气,传达当局的指示,总之,聚拢同心同德者,有效抗击残害我们的病魔’。而事实上,过不了多久,这家报纸就仅限于刊登广告,宣传新制的预防鼠疫的特效药了”。
“所有这些勤务都需要人手,始终处于告急的前夕。这些护士和掘墓人,起初都是政府员工,后来便临时聘用,他们许多人都死于鼠疫。不管采取何等防护措施,总有一天要受到传染。不过,真要仔细想想,最令人惊奇的是,在瘟疫流行期间,自始至终也不缺少干这行的人手。最紧张的阶段,出现在鼠疫达到高峰之前不久,无论是干部,还是他所说的粗活工,人力都捉襟见肘。然而,正是从那时候起,鼠疫真正席卷全城,猖獗到极点,完全打乱了经济生活,反而带来了解忧的后果,造成了大量失业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失业者不是聘用干部的来源,但是应招干粗活的则大有人在。的确,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显见贫困比恐惧更厉害,尤其是干的活越危险报酬越高。各个卫生组织都有一份求职者名单,位置一旦空出来,立即通知名单上靠前的求职者,他们肯定会招之即来,除非在此期间,他们也腾出了在世间的位置。要不要利用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犯人干这种活,省长犹豫了很久,现在就能避免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了,他认为只要有失业者,就可以等等再说了”。
“他们喝啤酒还是护理病人,终日懒洋洋的还是忙得疲惫不堪,整理登记卡片还是放放唱片,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别的差异了。换言之,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不再有所选择了。鼠疫已消除了价值判断。这种情况可见之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注重购买的衣服或食品的质量了。大家都全盘接受一切了”。
“灾难初起和结束时,有人总要耍耍嘴皮子。灾难初起的时候,这种习惯还未丧失,等到灾难结时,习惯又已经恢复了。只有在灾难最严重的时候,大家才实事求是,也就是说保持沉默了”。灾难初起时,流言与八卦让人们兴奋谈论;灾难结束时,人们劫后余生,要讲的故事太多,添油加醋,逢人便说;只有灾难最严重时,人们才会沉默,因为言语在此时最苍白无力。
“鼠疫初起那段时间,他们为一大堆自己十分看重的小事而苦恼不堪,生活中丝毫也不关心他人,只一味体验着个人生活;现在则相反,他们的兴趣完全放在别人感兴趣的事情上,头脑里只有公众的想法了”。疫情之前,我们每个人更多关注自己,而疫情时期,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刷新闻和抖音,看看大家和社会。
可惜,事实上,这个鼠疫是作者虚构的,作为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的奥兰确实发生过鼠疫,不过不是作者所说的年代,而作者本人也没有经历过。这恰恰又是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不论社会、人心等在疫情下的变化和描绘,都极其真实。
第二个感受,是两个触动心灵的情节。作者其实在小说里阐述了自己对于基督教和死刑的看法,可后者并没有给我太多触动,而前者却惹人深思,这是其一;其二便是格朗这个普通的公务员病重后,他的女骑士的形容词救了他,然后在失去形容词后,他又重获了新生。
其一,帕纳卢神父第一次布道演讲时说鼠疫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然后他目睹了一个孩子痛苦地死于鼠疫的全过程。因为孩子是无罪的,尚未开始人生的孩子是不可能因为“赎罪”而承受灾难、承受痛苦的,所以首次布道的观点产生了瑕疵,在非黑即白的观念下,导致人们怜悯孩子的情绪转变为上帝信仰的动摇。为防止人心动摇,神父决定进行第二次演讲,但他其实并没有解决这个矛盾,而是尖锐地指出,上帝只有信与不信,不信你敢么?不敢就信,然后再尝试让自己理解上帝做这个表面看起来不公正的决定自然有他的道理和奥义,理解的过程便是修行和参悟的过程。
比起第一次布道演讲,神父这次的语气则更加温和,也更为审慎。而且,他也不再讲“你们”,而是说“我们”。这是继另外一个城市的记者朗贝尔后,又一个局外人被纳入了鼠疫这场灾难的共同体中,只是不同于朗贝尔的身体不离去,神父则是摆脱了宗教赋予信徒的一种精神上的疏离感。
加缪说,如果灾难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宗教会被逐渐解构,换之而来的是迷信。“大多数人,即使没有完全弃绝他们的宗教义务,或者,即使没有参加礼拜的同时又过着极不道德的私生活,他们也会用一些毫无理智的迷信来取代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们宁愿佩戴护身圣牌或者圣罗克护身符,也不肯去做弥撒了。举例便可说明,我们的同胞开始滥用预言了。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有人开始担心,这场灾难真的没有头了。于是,瘟疫停止流行一下子就成了众望所归了。占星术士或天主教圣徒的各种预言,就这样一手传一手。可见,在我们同胞的心目中,这种迷信替代了宗教信仰”。
苦难会逼人直面终极选择,要么彻底交付信仰,纵身跃入信仰的深渊,要么全然拒绝虚妄,清醒地背对神明。而安逸才会使人停留在暧昧的中间地带,用半信半疑的妥协消解生命的重量。也许只有在绝境的时刻,人才能清楚自己是否有勇气做出绝对正确的选择。神性不再以慰藉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热焰般的极端要求烧毁所有伪善,嗯,真正的信仰或彻底的无神论,都是近乎疯狂的纯粹。
另外,如果鼠疫是上帝降下的处罚,那么得了鼠疫是否需要看医生呢?这是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呢?所以,神父死于鼠疫。
其二,格朗病重。他吃力地眨了眨眼睛,”这次我若能幸免,大夫,那就脱帽致敬!”然而,他随即就跌入衰竭状态。“脱帽致敬”这四个字,是看本书的唯一一次眼含热泪。抱歉,每天百余人的死亡,只是个没有情感而冰冷的数字,并没有让人落泪。
格朗要求将放在抽屉里的手稿拿给他,说话的声音异常虚弱。塔鲁拿给他手稿,他接过去看也不看,就抱在怀里,随后又把手稿递给大夫,打手势请大夫念一念。手稿仅有短短五十来页,大夫翻了一下才明白,每页稿上都是同一句话,没完没了重新抄写,修改和增删。”五月””女骑士””林间花径”,这些词不断地出现,但是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这是他生命的希望,这些关键词在他大脑里盘旋,希望变得渺茫,他想找到最佳组合为希望增加抵抗力,抓住日益缩减的希望。
最后,格朗奇迹般的恢复。临上楼的当儿,他对大夫说,他已经给雅娜写了信,现在心里释然了。另外,他又重新写了那句话,并且说:“所有形容词,我全部删掉了”。他终于不再纠结于各种形容词、纠结于每个词语所表述的恰当性,而勇于直面世界了。
第三个感受,是四个清晰映入大脑的画面。
一是里厄和塔鲁在屋顶平台之上。他们上去一看,平台已空无一人,放了三把椅子。从一面极目望去,只能看见平台连着平台,最后靠着一个岩石般的、幽暗的庞然大物,他们认出那是第一座山丘。从另一面望去,目光越过几条街道和看不见的港口,能落到海天一线,依稀颤动的天际。他们看不到光源的一束亮光,从他们知道的悬崖后面有规律地再现:那是航道的塔灯,从春天起,就一直指引航船改道驶向其他港口。大风清扫过的天空很清亮,纯净的星星闪烁,远处灯塔的光束不时掺杂进来,好似掠过的一缕青烟。微风送来花草的芳香和石头的气味。周围一片岑寂。天气真好,里厄坐下来说道,就好像鼠疫从来没有蹿升到这里。
二是疫情结束后的火车站台上。于是,亲人相拥着各自回家,视而不见周围的世界,表面上战胜了鼠疫,置之不理一切苦难,置之不理同车来的人还有的不见一个亲人,准备回家确认久无音信已经在他们心中滋生的忧惧。中午,太阳战胜了从清晨就在空中与其搏斗的寒风,向城市不间断地倾泻着静止不动的光芒。白昼停滞了。山头要塞的大炮不断向入定的天空轰鸣。全居民倾巢出动,庆祝这一令人激动万分的时刻,而在这一时刻,痛苦的时期结束了,遗忘的时期尚未开始。
三是作者想象出的若是疫情再持续久些政府职能丧失后的画面。染病的人就会死在尸堆上,腐烂在街头,全城有目共睹,眼看着垂死者在广场上紧紧揪住活人不放,那种举动混杂着合乎情理的仇恨和愚昧透顶的希望。
四是异地隔离的记者坐在咖啡馆里。暮色好似灰暗的水流,漫进了餐厅,而天空的晚霞映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餐桌面在开始暗下来的厅里隐隐发亮。咖啡馆里空荡荡的,朗贝尔在那里,活似一个游魂。
值得一读。但不要读李玉民翻译的版本,读着费劲。丁剑翻译的要好些。
no comment untill now